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是事后的帮助行为,行为人的掩饰、隐瞒行为应当发生在上游犯罪已经既遂或者虽然未遂但犯罪行为已经结束之后,行为人在本犯既遂之前故意参与,并在事先、事中就对上游犯罪起到参与、配合、协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如事前与盗窃、抢劫等犯罪分子通谋,形成了共同犯罪故意的,其客观上的掩饰、隐瞒行为就成了共同犯罪的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的犯罪分子通谋的,以共犯论处。
![图片[1]-灵宝市刑事辩护律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上游犯罪共犯的界限-陈晓峰律师网](https://www.cxfls.cn/wp-content/uploads/2024/08/微信截图_20240821205533.jpg)
资深刑事辩护律师、从事刑辩业务多年的陈晓峰律师【15188506266】解答:
但是,需要注意区分承继的共同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犯罪的既遂、未遂形态对其区分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本犯实施了犯罪行为并取得了赃物,但是还没有达到既遂时,行为人参与其中,应成立共同犯罪。如明知是他人盗窃的存折、信用卡而去取钱,此时,盗窃存折、信用卡的行为因为未取钱或使用并未达到犯罪既遂,行为人取款或使用的行为应作为盗窃罪的组成部分,从而认定为盗窃罪共犯而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图片[2]-灵宝市刑事辩护律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上游犯罪共犯的界限-陈晓峰律师网](https://www.cxfls.cn/wp-content/uploads/2024/08/02.png)
但在具体认定时,应当注意稳定的赃物收购关系这一情形。如甲是一名电动车收购人员,明知乙送来的电动车是盗窃所得并予以收购,并经常打电话询问乙是否有“新货”来卖。此时,虽然甲在乙实施盗窃行为之前就与其达成了事后处理赃物的共识,但其并不构成盗窃罪,而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原因在于,甲在事前的询问并不能说明两人存在犯意联络,因为其对乙的具体盗窃行为、具体盗窃地点、具体盗窃时间并不了解,没有共同参与盗窃行为的主观意图,这里的询问只能用以说明甲对乙的赃物性质有主观上的确定性明知。如果把主观上对对方犯罪活动的明知认定为“事先通谋”,将会不适当的扩大共同犯罪故意的领域。
![图片[3]-灵宝市刑事辩护律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上游犯罪共犯的界限-陈晓峰律师网](https://www.cxfls.cn/wp-content/uploads/2024/09/微信截图_20240919214800.jpg)
另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属于上游犯罪的事后帮助犯,其最高刑期为七年有期徒刑,整体上具有“罪小刑轻”的特点。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进行量刑时,必须要注意与上游犯罪之间的量刑平衡。一方面,本罪对上游犯罪有依附性,没有上游犯罪取得的财物,就没有下游犯罪可言;另一方面,本罪处罚的重点在于妨害司法秩序,并没有扩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与事先参与犯罪共谋的情形相比,社会危害性要小一些。因此,在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进行量刑时就必须要考虑上游犯罪的量刑,在二者指向同一对象的情况下,本罪量刑应当轻一些、从而适当拉开档次,避免上下游犯罪量刑不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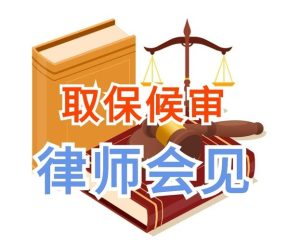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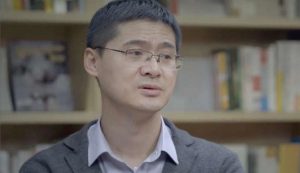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